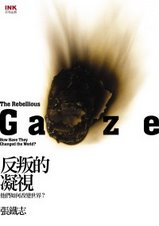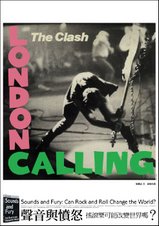而不知是因為天氣太惡劣,抑或是路上太冷清,總覺得寒冷刺骨。
一走近/進這個建築,就可以立即感受這個地方的特立獨行:在教室般大小的場地,一切都是如此無所謂:賣票的人,桌椅的擺設,以及如果稱的上裝潢的裝潢。只有台上的鋼琴、大提琴、吉他兀自安靜地坐著,等待開場。
這裡是Tonic:一個揉雜著實驗、前衛、另類的爵士樂或流行樂的表演場地;紐約過去幾年音樂革命地景的最前沿。
這裡是下東區,紐約殘存的少有觀光客但卻是最具文化生命力的地區之一。從紐約發展早期就有大批各國移民,而過去半個世紀,更有許多詩人和音樂人蟄居在這個紐約少數尚未被資本主義吞噬的街廓。而現在,則有越來越多風格化的藝廊、咖啡店和表演場所隱藏在其中。
這裡是紐約,不論是爵士樂、前衛音樂以及民歌、搖滾或電子──從六0年代的民歌和地下天鵝絨(Velvet Underground),到七0年代的叛客到這兩年興盛的車庫搖滾;或者是七零年代以來爵士樂、前衛音樂與搖滾樂的跨界激盪,這裡始終是西方音樂革命的起點,風暴的中心。
而這些堅持探索音樂可能性的創作者,就是誕生、孕育於這一間間的表演場所。他們或許簡樸、破敗、甚至污穢,但總是能被不斷湧現的勇氣和才氣點起炫麗的火花,然後開始在世界燃燒起新的光亮。
今日我的第一次到來,迎接我的是完全沒聽過的一個在地樂團。
當一位略顯豐滿、頭髮凌亂,且略帶滄桑的中年女子走上舞台時,我實在難以預期接下來會看到什麼樣的表演。
這位女子帶我們坐上衰老的紐約地鐵,回到她兒時成長的地方:康尼島(Coney Island):一個紐約近郊的海濱遊樂園,曾經輝煌於二十世紀初,是無數孩童的夢幻遊樂園;如今雖然還在運作,卻已年華老去,只剩摩天輪在海濱旁百無聊賴地轉動著。於是,當她的樂隊(一人是小提琴,另一人是電子琴兼鋼琴加鼓)演奏起遊樂園的配樂,她遂以雲霄飛車般從低沈直奔高亢的不可思議之聲,帶我們穿越一場場略帶頹廢卻讓人屢屢驚呼的費里尼式音樂嘉年華:是紐奧良的小酒館藍調,是西班牙的熱情舞曲、是Kurt Weill的劇場音樂,或者就是Tom Waits扮起女妝,在這個紐約的下東城,吟唱著那些遊蕩在灰冷冬天與斑駁摩天輪下一顆顆老靈魂的故事。
第二次的Tonic之行,則彷彿是參加一場神秘派對。這場門票只要六元美金的表演開始於午夜十二點,表演者是Vincent Gallo---身兼導演/演員/音樂人的獨立文化界怪傑,加上約翰藍儂和小野洋子之子的Sean Lennon。而小野洋子這位歷史傳奇人物,正坐在角落靜靜地欣賞小小舞台上兩人對彈吉他:冷調的緩飆與不時的低吟,的確讓人憶及幾年前在金馬國際影展看到Vincent Gallo成名電影「Buffalo 66」中,那個嚴寒小鎮被風雪冰凍的寂寞。
Tonic,新的音樂革命就從這裡開始。